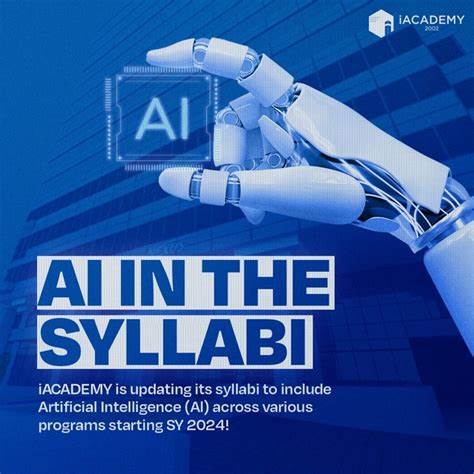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AI正逐步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教育领域,其影响愈加显著且复杂。高校,作为知识生产与思辨的核心阵地,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如何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大潮中保持独立思考的灯塔作用,防止教育的工具化和技术化带来的人文精神和批判能力的流失,成为高校必须思考的问题。高校的角色不仅仅是被动接受AI带来的变革,更重要的是积极担当起对AI泛滥的抵制与反思,捍卫教育的本质价值。人工智能技术并非凭空出现,它的诞生和发展与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密不可分。过去数十年间,教育经历了市场化、指标化和机械化的过程,学术活动逐渐被简化为可量化的成果和标准化的流程。
教育技术(Ed Tech)的推广,一直倡导学习是信息的传递而非关系的构建,这种观念为AI的介入提供了土壤。面对如此局面,大学在维护教育多样性和关系性价值方面理应发挥更大作用。正如思想家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在其著作《共生的工具》中提出的观点,工具的意义远超单纯的物质载体,教育本身即是一种“工具”,不仅是传递知识的机器,更是塑造人类关系和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复杂的技术工具及其所承载的庞大机构体系,其影响力不容忽视。AI以其神秘且难以预判的内部机制,依赖大规模的数据和运算资源,形成了消耗能源、材料和全球资源的巨大基础设施。同时,AI的发展和应用过程常伴随剽窃大量文本、图像和声音数据,这对创意产业和知识产权带来直接威胁。
高校应当敏锐地意识到这种规模扩张带来的深层社会影响。AI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往往被包装成革新教学法和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工具。然而,AI生成的内容并非真正的总结或研究,反而是基于已有模式的预测和重复,缺乏批判性和创造力。这种“拟态”产出无疑带来了“泥浆化”的风险,使学生和教师的认知能力出现退化。同时,AI在教育中的应用实际上推动了劳动的更加碎片化和私有化,加剧教师和学生的焦虑和不安。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机构的深度绑定,包括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加州州立大学以及爱沙尼亚中学体系在内的多家高校,正“购买”AI工具计划,将学生和教职工纳入技术化管理轨道。
这种现象引发了伊里奇关于“激进垄断”的警示,即当工业化生产过程通过独占满足某些迫切需求时,会剥夺人们自主从事非工业化活动的能力,进而控制人的生活方式。高校应警惕AI工具成为教育的“激进垄断”,压制原本应存在的自主学习和创造能力。在培养批判性思维方面,AI的介入同样存有巨大隐患。大学推广基于AI的快速反馈和作文辅助工具,极易让学生减少动脑思考的过程,弱化探究精神与独立判断。批判思维无法通过统计学方法获得优化,真正的反思需要摩擦与挑战,依赖人与人之间的复杂互动和深度理解。AI模型去年被应用于主流媒体中进行“平衡”意见的尝试,结果却出现对有害言论的文化合理化与误读,暴露了技术介入公共话语的危险性。
对学生而言,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当他们走出校门即面对由AI驱动的招聘系统、报告生成和心理咨询服务,他们的认知和情感状态或许早已被技术操控。英国青少年中近半数宁愿回到无互联网时代的调查结果,足以反映算法和AI带来的心理危害。高校若不质疑AI的教育效用,并努力抵制其负面影响,极可能是在主动损害下一代的学习体验和精神健康。尽管如此,政府部门和主流舆论对AI的推广意愿强烈,以英国现任政府为例,发布了雄心勃勃的AI行动计划,强调科技驱动的经济增长,甚至将电力供应和土地划为所谓“AI增长区”,以吸引数据中心和技术企业投资。然而这种对AI的盲目追求,可能会加深社会不平等和自治权丧失,甚至带来算法歧视和政治操控的隐患。高校应成为这场竞赛的理性守护者,保持对AI扩张的警醒姿态。
针对如此境况,大学理应承担起反抗的使命。抵制AI不仅限于技术自主的呼声,更应涵盖对环境可持续性、创意权益保护以及去殖民化视角的深刻反思。正如伊里奇所倡导的“反偶研究”,高校应致力于揭示和阻止工具背后潜藏的“杀戮逻辑”,发展能够促进个体自由与社会生命力的共生性工具和系统。对AI的批判必须建立在对工具社会意义的研究与公开讨论上,推进技术的社会决定权,使教育不再成为AI商业化的附庸。具体实践上,成立“人工智能人民议会”或“师生联席委员会”可为高校提供一个平台,允许全员参与对AI的严谨质询,并借此修复因技术介入产生的师生怀疑与隔阂。此类组织不仅能评估AI应用的适应性与公平性,还能连接校外受AI负面影响的行业和群体,共同推动多层次的技术社会审查。
此外,面对AI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渗透,更需要跨学段教师团结合作,共同挑战这一“AI泛滥”的趋势,避免整个人群的未来被“AI烹饪”得体无完肤。在抵制AI的过程中,大学应该成为批判思维与想象力的孵化器。AI带来的技术政治变化不仅仅是市场掌控的展现,更是一种全球资源掠夺和意识形态统治的体现。高等教育的抗争正是要激活那些反抗权威主义和技术极权化的能力,塑造社会多元包容和新型共存的可能性。学生群体往往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大学作为他们的成长环境,应提供滋养独立思想和集体希望的空间,避免被技术生态中的冷漠与计算所侵蚀。总的来看,高校必须拒绝成为技术“必然性”的附庸,主动践行严谨的批判教学和社会责任,培养能质疑、能创造、能共情的未来公民。
人工智能虽然在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但唯有通过对其不断反思、质疑与约束,才能在智能时代中保护人类的自由与尊严。只有内含理性抵抗的大学,才能真正成为推动社会向善、促进人类共生的坚实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