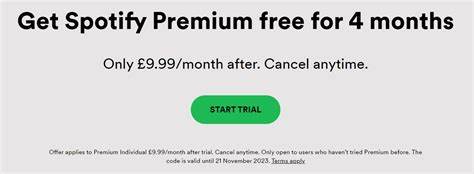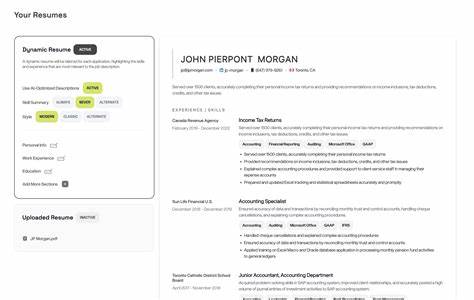近年来,私营慈善资金大量流入科学与医学领域,多家基金会如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威康信托基金、新诺丹斯克基金会和盖茨基金会等,均拥有超过两百亿美元的捐赠资本,主攻科学研究。然而,这些资金分配往往依赖庞大的官僚体制,资助者需详尽说明项目的可验证影响力,研究方向多聚焦于传统一流学术机构,导致资金去向高度趋同。众多财富巨头如默克前CEO罗伊·瓦杰洛斯向哥伦比亚大学一次性捐赠九亿美元,基金用于基础生物医学研究机构。对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系的三亿美元捐助,使其冠以捐助者肯·格里芬之名。耐克创始人菲尔·奈特多次以数亿美元支持俄勒冈卫生科学大学与俄勒冈大学相关科研项目。尽管钱数巨大,但资金使用的路径与策略大多维护和强化现有体制,没有真正开拓新的研究范式或机构体系。
相比之下,历史上慈善的运作更加多样化,许多科学成果正是诞生于这些非传统的资助模式。著名科学家卡塔琳·卡里科的突破性mRNA疫苗研究,曾被正统资助方冷落,多亏私人支持才得以发展和应用。疫情期间她的经历暴露出现有资金机制的限制,显示出"疯狂慈善"的潜在必要性。所谓疯狂慈善,是指对那些非主流领域、学术体系外的个人和颠覆性创新项目的支持。这种资金模式往往带来更大风险,更易出现失败甚至浪费,但也助推了前所未见的技术与理念诞生。有意义的,如帮助寻找"下一个卡里科"的新兴科学团体Analogue Group和Convergent Research,将资金投入边缘领域,培养原始创新人才。
即使是新兴慈善机构,也多多少少沿袭现有学术体系,如HHMI的研究员项目,虽相较传统拨款自由度更高,依然依赖现有专家与机构进行评估和管理。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长远拨款模式未能真正跳出体制,依旧围绕大学内的顶级科学家展开。而诸如帕克癌症免疫学研究所和陈-扎克伯格生物科学中心等,虽强调合作和创新,但实际上它们与顶尖大学紧密关联,学科和研究模式基本延续主流。学术机构设计上的同质性被社会学家迪马吉奥与鲍威尔称为"制度同构",其背后原因包括法律法规的强制性、模仿行为驱动和职业规范压力。尤其在资源、人员和合法性高度依赖相同渠道时,机构趋向高度一致。自19世纪末斯坦福大学和加州理工等高校建校以来,科学机构在组织结构、等级体系及研究范畴上逐渐形成统一模式。
纵使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多变,学界体制却相对僵化,对拓展多元化、破范例的学术实验空间造成阻碍。早期私密慈善则呈现诸多不同面貌,尽管充满不确定性和失败风险,但也为后来的重大科研突破奠定基础。如莱布尼茨在17世纪受私人资助研究家族族谱,虽添烦恼,却保障其能持续科研。20世纪初美国富商乔治·法比安建造了私人大型实验室,扶持了克里普托图学开拓者弗里德曼夫妇,他们的研究成果间接催生了国家安全局。阿尔弗雷德·卢米斯则在1930年代用自有资金打造实验室,造就雷达和核反应堆等关键技术,极大推动二战科技发展。历史告诉我们,疯狂慈善的魅力在于放飞创新想象,容忍失败,善于捕捉意外机遇。
如今,虽然数百亿美元流入科学领域却仍旧模式单一,但仍有极少数富豪投入极具风险的独特项目。硅谷创业家纳特·弗里德曼利用机器学习竞赛解读庞贝火山遗留下的古老手稿,高奖金额激励新兴人才。另一例是游戏公司Valve创始人盖布·纽维尔投资建造海洋研究船,支持对深海的前沿探测,计划向全球免费共享发现。哈佛天文学家艾维·洛布创立伽利略项目,大胆探寻外星人迹象,虽受学术界质疑,却依靠加密货币和科技界支持,得以尝试非常规科学视角。未来,疯狂慈善或许需要更多来自多元领域的支持者主动承担风险,关注被主流忽视的科学。这不仅仅是动员资金,更是挑战现有科学生态的教条与框架,激发跨界和创新精神。
诸如人体解剖学等"老"科学领域依旧存在盲点,充足且创新型资金支持可带来新的认识突破。此外,探索地外生命、深海未解之谜、古文献解读等领域,无疑是无限可能和高风险并存的前沿。疯狂慈善鼓励投资者超越既有体系的束缚,勇于支持那些看似偏门,却具备颠覆潜力的科学研究。极大提升了科学进步的多样性和可能性。推动科学发展的驱动力不仅仅来自政府和科研机构,更依赖于个人勇气与非传统模式的探索。总结来看,现代科学资助体系的高度制度化司空见惯,必须用更加开放且富有冒险精神的私人慈善激发新创意、新突破。
疯狂慈善正是唤醒科学活力与多样性的关键。只有打破现有官僚壁垒,激励更多支持非主流科研,才能真正促进科学伟大进步和社会福祉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