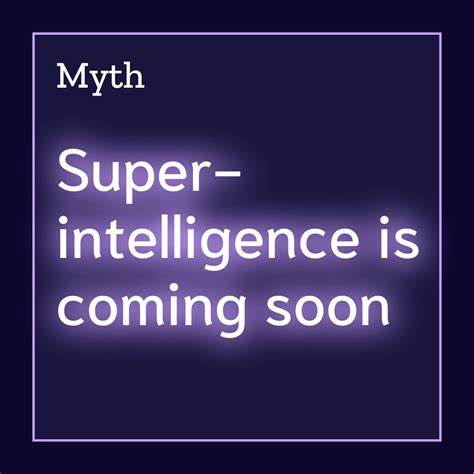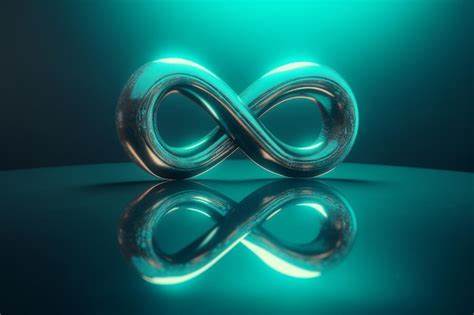在人类技术史上,每一次科技突破都伴随着对未来的幻想与恐惧。核武器的发明不仅改变了战争的形态,也引发了对文明未来的深刻反思。时至今日,人工智能(AI)的迅猛发展再一次将我们带到了一个类似的十字路口。与当年物理学家们对原子能量的探索相似,当今科技巨头与投资者争相投入资源竞速于“超级智能”的研发,其背后既有技术热情,也夹杂着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博弈。然而,这场关于超级智能的争论是否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超级智能真的将超越人类,为我们带来福祉,还是一种被误解和神话化的幻象? 所谓的超级智能,最著名的定义来自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他在2014年的著作《超级智能》中提出,这种智能体将在人类感兴趣的几乎所有领域远远超越人类的认知能力。博斯特罗姆设想了一个可以递归自我改进的系统,即它能够不断重写自身结构实现指数级智能提升,最终达到令我们难以理解和控制的阶段。
这种构想引发了广泛关注,许多声音警告智能失控的风险,提出了诸如“纸夹最大化者”等科幻式情景,表达对机器无情优化目标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恐惧。 然而,现实远比这些极端设想更复杂。当前被称为“超级智能”的大多数系统,实际上只是在人类特定领域显示出超越常人表现的“超性能”,如在围棋、图像识别或语义理解方面展现出惊人的能力。这种“超性能”不等同于真正意义上的智能。智能不仅是速度和准确度的堆叠,更是一种涉及判断、适应、创造以及理解意图和价值的复杂能力。现实中,人类乃至自然界的智能表现多样且难以量化,不同生物种类展示出形态各异的解决问题方式,体现了智能的多样性和情境性。
将智能简化为可测量的分数或任务表现,是知识生产过程中常见的陷阱,也是一种深刻的误读。这一误读起源于历史上对智力的简化测量,例如十九世纪的颅骨测量、二十世纪的智商测试,这些方法在当时不仅缺乏科学性,还被用以支撑种族歧视和社会阶层的划分。如今,超级智能的神话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这种以数字化标准衡量智能的传统。通过设置各种基准测试和排行榜,我们在无意识中加剧了认知狭隘,忽视了智能本质中的情境性、关系性和多样性。 科技的不断进步使得我们确实能打造出以惊人效率处理特定任务的算法和模型。这些系统擅长模式识别、数据预测和语言生成,但它们缺乏人类固有的“认知代理”(epistemic agency):即主动提出有意义问题、重新框定问题、解释证据和决定何为知识的能力。
换言之,这些机器是工具,仍需人类引导选择研究方向和赋予价值判断。对外界的关注、同理心和伦理选择,是目前任何AI都无法真正拥有人类层面的复杂智能特质。 媒体报道时常放大AI的突破,渲染其具备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但背后往往是人类专家的积极参与和引导。例如,对于数理难题的突破,AI充其量是强力的辅助工具,而非独立的发现者。这样的夸大容易滋生对机器超越人类智能的幻觉,从而强化超级智能的神话,误导公众和政策制定者。 过度依赖这种狭义的智能定义,不仅对理解人工智能的现状带来偏差,也在社会层面造成深远影响。
教育体系中,学生面对写作检测算法而非批判性思考,知识学习趋于机械化和标准化。招聘系统里的AI偏向强化已有偏见,排斥多元声音,反映了数据和算法背后的结构性不公。医疗领域,因训练数据缺乏多样性,一些AI诊断工具未能准确覆盖不同族群,进一步加剧了健康不平等。 此外,AI对文化和认知的影响不可小觑。传统知识体系、土著智慧、集体记忆和神经多样性等非主流的认知方式,正因不符合同质化的测量标准而逐渐被边缘化。这种文化与认知的单一化,可能导致创新力和社会韧性的大幅削弱。
我们正目睹一个智能被资本和技术垄断重新定义的过程,由少数科技巨头控制着数据信息流和算法规则,牵一发而动全身地塑造社会结构和公共认知。 真正值得警惕的并非AI本身的能力是否会超过人类,而是我们如何框定智能的意义,以及因此而选择投资和塑造技术的方向。智能不仅仅是算法的速度和正确率,更是一种关系性的能力:与世界、他人、甚至自身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共处的艺术。智能是体现于判断力、共情、反思和创造力的整体表现。人工智能目前仍然属于被动的执行者,而我们必须警惕将这种被动工具神化为控制和智慧的象征。 在重新认识智能的过程中,学界和社会各界已经展开反思和实践。
教育领域,一些社区正回归本土教育,重视故事、关系和环境;科学界崇尚慢科研,强调关怀驱动的探索;伦理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推动更加公开参与的AI治理,确保系统的建设尊重多样利益相关者;生态和认知学研究日益关注网络、群体和非人类智能形式的启示,从真菌网络的智慧到口述历史的代代传承,都在挑战单一化智能观。 未来的路径不应是人类与机器的竞速,而是智能的多维共生。人类需要认识到,智能是一场共舞,是分布在身体、系统、生态和时间之中的复杂现象。唯有摆脱那狭隘、被资本和权力驱动的智能标准,我们才能打开智能的多样性,重建知识的多元生态,维护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总结来看,超级智能的神话更多反映了当代社会的认知焦虑和技术幻想,而非科学事实。它牵动着资源分配和权力结构,却可能遮蔽我们对真正智能的理解与尊重。
打破这一神话,不是拒绝技术进步,而是要求我们更深刻地反思智能的内涵,拒绝用单一指标衡量复杂能力,警惕技术对社会的狭隘塑造。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迎来一个技术与人文共荣、包容多样智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