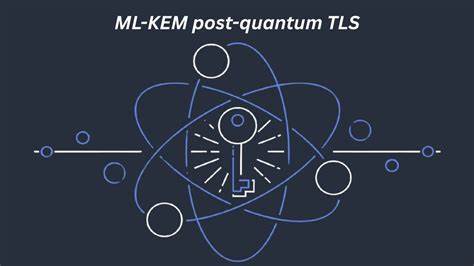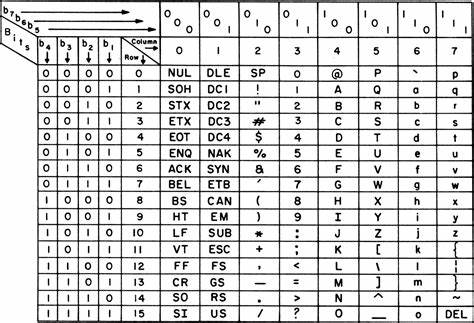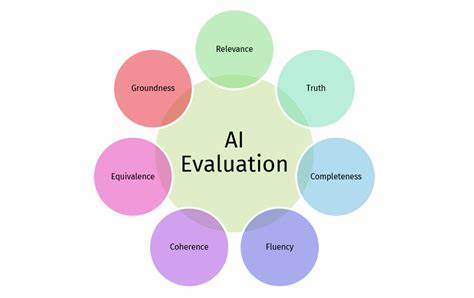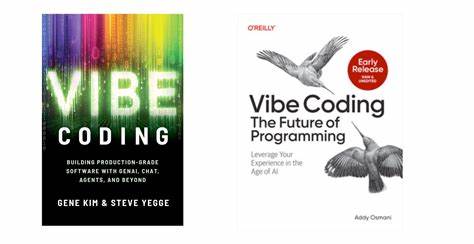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进展让许多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无论是英伟达的黄仁勋,还是AMD的苏姿丰,甚至是OpenAI的负责人Fidji Simo,他们无不对人工智能充满了极大的热情和信心。然而,这种看似积极的态度背后,却隐藏着对人类创造力和人文精神的潜在忽视,甚至可以称之为一种“反人类”的倾向。这种现象的根源,或许正是现代社会深受启蒙时代思想影响的产物。 启蒙时代以理性为核心,极力推崇科学技术的力量,力求通过理性进步实现人类社会的“理想国”。许多科技CEO的AI狂热,正体现了这种启蒙理念的延续。
他们期盼通过科技超越人类固有的限制,实现所谓的“技术乌托邦”,在这过程中,人文科学被边缘化,传统的人类价值观念被重新审视甚至挑战。苏姿丰在一个AI峰会上提到,未来的教育应突出科学技术,以培养适应AI时代的新一代人才。在表面看来这是合理且必要的,但在她和其他同类主张的影响下,文科教育正在被挤压,甚至呈现出削弱趋势。人文学科作为研究人性和社会文化的学科,其本应是人类理解自我的重要渠道,正面临缩减甚至被忽视的风险。 很多时候,AI推广者将创造力简化为“想象力”,而忽略了真正的“创造”过程。这种观点认为,只要有人能想象出作品,实际的执行可以交由AI来完成。
OpenAI的负责人菲基·西莫便表达过类似理念,她认为AI让所有人都能轻松实现脑海中的图像和创意,将艺术创造门槛大大降低。尽管这为许多人提供了便利,却也隐含着对传统艺术创作过程的淡化甚至轻视。真正艺术家的价值不仅在于灵感,更在于耐心、技艺和对细节的把控,这些都是AI难以复制的。黄仁勋则将人工智能称为“伟大的平等器”,强调每个人都能成为艺术家、程序员或作家。这种看法的极端解读可能导致社会对专业技能和长期积累的忽视,弱化人类劳作的独特价值,最终导致对人文参与和人文知识的轻视。 AI狂热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后人类主义的趋势。
现代科技发展试图突破人类的生物极限和理性限制,将人类存在视为可以被超越和替代的阶段。未来学家瑞·库兹韦尔描绘的“奇点”预示着人类与机器的融合或超越,这种愿景既激动人心,又令人警惕。它潜在地威胁到人类作为独特存在的地位,将人类认知和创造归结为可复制和被替代的代码和数据。 这种理想背后,隐约可以看到启蒙时代对理性的绝对信仰以及对科学无尽进步的盲目信念。哲学家约翰·格雷指出,启蒙运动推动了对理性的崇拜,寄希望科学能带来理想社会。终极目标通常是造就一个科学至高无上的“乌托邦”,在这个过程中,人文关怀往往被视作“非理性”或“过时”。
这种“进步主义”的信仰持续延续至今,无论是极端的政治运动还是现代科技发展,都带有这种宗教般的救世主情结。 面对AI带来的挑战,社会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是真正的人类价值。当今的AI狂热为我们敲响警钟,提醒人们技术发展不能仅仅成为机械式的效率提升,而必须结合人文思想,关注人类的情感、尊严和创造力。正如哲学家戴瑞福斯和凯利所言,我们应当重新“赋予世界神秘感”,停止将自己简单地视为技术工具,恢复对生活中各种意义的敏感性。这种“玩艺儿精神”在电子游戏中得到体现,许多玩家珍惜游戏过程中真正的人际交流与创造性劳动,而非单纯追求快速的结果和机械反应。 在教育领域,保护和强化人文学科的地位同样重要。
人文学科负责培养批判性思维、伦理观念和文化理解,这些是纯粹技术训练无法替代的。未来的教育应当兼顾STEM与人文,促进多元化的发展,培养既懂技术又理解人性的复合型人才,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仅仅讨论AI监管远远不够。围绕AI的社会影响,我们必须展开更深层的伦理和哲学反思。这不仅关乎如何制定规则,更关乎我们如何定义“人类”,以及在技术进步面前如何坚守人类价值。只有重新审视人类存在的意义,科技才能真正成为赋能而非取代人类的力量。
总结来看,科技CEO们对人工智能的狂热虽然推动了技术飞跃,却也可能在无意识中助长了一种反人性的生态。以机器替代人类创造,以效率取代理性和情感,甚至以技术乌托邦取代多元价值的未来,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对人类和技术关系的理解,不只关注技术本身,而应重视人类的主体性、创造力和生命的独特体验。唯有如此,才能避免陷入由启蒙理性驱动却忽视人的未来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