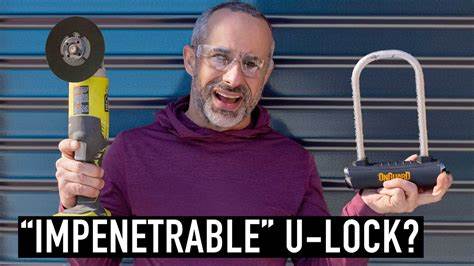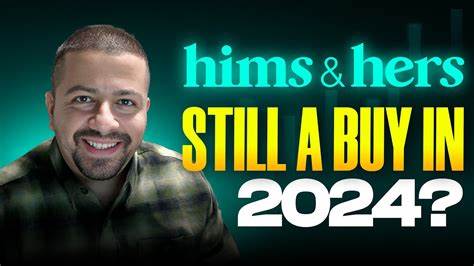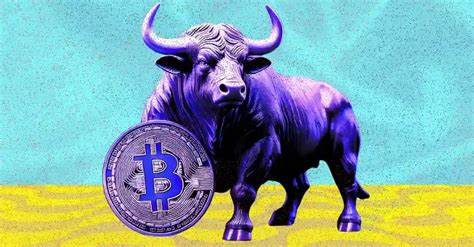在美国社会,围绕“天才少年”和“伟大人物”的神话故事已经深入人心,这种对单一领导者的崇拜和英雄化叙事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结构性的危机。美国几乎从建国之初就形成了一种迷信领袖和少数成功男性的文化,将他们塑造成社会进步的唯一推动者。如今,这种文化仍在科技、商业乃至政治领域中不断延续,但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让社会陷入深刻的矛盾和分裂之中。 首先,美国社会对所谓“男孩天才”的狂热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问题。年轻的创业者如马克·扎克伯格、埃隆·马斯克和过去的亚当·纽曼等人被包装成神话式的天才人物,他们的故事充斥着传奇色彩和英雄主义叙事。无论是社交媒体、电影还是纪录片,这些故事都将成功简化为单一的个体努力与天赋的体现,忽略了背后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团队支撑和资源投入。
苹果用以命名的天才科学家牛顿,特斯拉以科学家的名字命名,这些都暗示了科技领域领袖的“天才光环”,让公众自然地将企业的成功归功于个人而非集体的努力。 然而,这种对创始人和领导者的迷信忽视了一个核心事实:他们并非孤立的英雄,而是高度依赖资本市场和投资支持的群体。以WeWork的创始人亚当·纽曼为例,他以“资本主义集体农庄”般的理想包装自己的公司,最终却因商业模式的严重不合理性和草率扩张而陷入崩盘。纽曼本人在公司破裂后居然拿到了高达17亿美元的“离职补偿”,这一金融操作不仅令人愤慨,更暴露出资本市场对少数“伟人”的特权纵容。 同样,费尔节(Fyre Festival)的失败故事,也凸显了这类“天才少年”创业故事背后的虚伪和欺骗。创始人麦克法兰借助社交媒体的营销狂轰滥炸,虚构出奢华音乐节的泡沫盛景,却让数千名消费者身陷食品短缺、卫生恶劣的混乱境地。
这个事件引发的巨大舆论嘲讽,反映出公众对这些商业英雄神话的双重情绪——既憧憬成功,也警觉其背后的潜在风险与欺骗。 更广泛而言,美国社会的“伟人崇拜”延伸到了历史的塑造上,尤其是对开国元勋的理想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历史人物,被文化产品如林-曼努埃尔·米兰达的《汉密尔顿》音乐剧赋予了现代英雄色彩。这类作品在文化上掩盖了原始历史的复杂性与冲突,比如汉密尔顿作为金融家,推动财富集中和反民主倾向的实质政治行为。音乐剧的高度商业成功恰恰反映出公众对他们塑造的“伟人”神话的接受度,这种神话成为维持现状并阻碍真正社会变革的文化屏障。 媒体和娱乐业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
编剧如艾伦·索尔金,凭借电影《社交网络》和《乔布斯》等作品,美化并强化了具有“天才加性格缺陷”的科技创始人形象。这些形象往往将道德困境和行为失当美化为“伟大”的代价,进一步巩固了公众对成功与“叛逆天才”之间必然联系的迷思。与此同时,现实中科技创业的众多阴暗面,包括投资欺诈和劳工剥削,却被故事屏蔽,因而难以得到应有的关注。 实际上,围绕“伟人”故事的迷信遮蔽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那就是财富和权力的高度集中。美国作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的现象异常严重。历史上由少数“伟人”发迹的资本家,几乎垄断了经济和政治资源。
这种权力和资本的交织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精英阶层,进一步阻碍了社会的公平和流动。正如许多批评者指出,美国的民主制度在这种现实中受到了重创,民主的活力开始褪色,贫富差距加剧,社会不满情绪高涨。 在政治领域,同样存在着对强人领袖的迷恋,从特朗普的两次总统任期到其在公共舞台上塑造的独特“强人”形象。这种领导者往往以直接、粗暴且极具操控性的手段赢得一部分选民的支持,而这种支持则以牺牲社会整体理性讨论为代价。美国社会在这类强人领导与传统民主制度之间摇摆,体现出社会深层矛盾的激化。 与此同时,普通民众和集体的力量往往被淡化甚至忽视。
社交媒体平台的成功绝非单个创始人行为的结果,而是数以亿计用户无偿创造的内容和流量推动了平台价值的增长。然而主流叙事中很少强调“用户”的价值,反而将焦点放在了所谓“天才创始人”的个人传奇上,每当这些创始人遭遇挫折或丑闻,公众情绪便出现复杂交错的反应:既有批判,也有某种程度的同情,有时甚至是盲目的支持。 对现状的质疑和反思正在逐渐萌芽。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打破“伟人神话”的迷雾,重新审视权力结构和社会财富分配机制。批判性地分析历史真相、倡导集体力量和制度改革正成为未来社会的关键议题。同时,针对科技行业的监管、垄断分解、税收政策改革以及工会运动,成为遏制财富与权力过度集中的重要工具。
在文化表现层面,对历史人物的多元化解读正逐渐兴起。更多学者重新审视开国元勋的复杂性,包括他们的种族、阶级和政治立场问题,促使公众走出黑白二元的“伟人”幻想,看到一个多面且真实的历史。在媒体和艺术制作中,也正逐渐推动平权叙事,强化普通人的存在感和主人翁意识。 美国对“天才少年”和“伟人”痴迷的文化根深蒂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复杂交织。但这种将成功和改变单纯寄托于某几位个人英雄的叙事,掩盖了不平等的根源和集体行动的意义。要想走出当前的困境,必须拆除这一神话建构,重建面向共同利益的社会共识与制度保障。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建立一个更公正、更具包容性的未来社会,真正实现人人参与和共建共享发展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