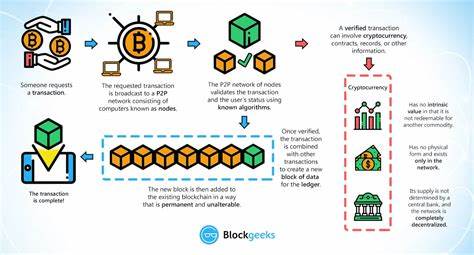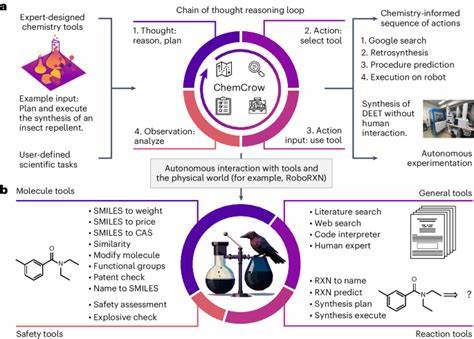在约旦首都安曼的街头,伊布拉欣·埃德里斯(Ibrahim Edris)的身影随处可见。他是许多行人的熟悉面孔,无论走到哪里,总能看见他热情地向街坊邻居招呼问候。他的问候语洋溢着温情——“as-salamu alaykum, habibi”,意为“愿平安与你同在,我的朋友”。虽然在约旦生活已逾十年,但他的心从未遗忘故乡达尔富尔的点滴。伊布拉欣和其他黑色难民的经历,揭开了在这片中东土地上鲜为人知却深刻的故事。约旦是一个难民接纳国,但黑色难民在这里过得并不容易,他们不仅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还被歧视和忽视困扰。
伊布拉欣的旅程始于十多年前,当时暴力与冲突迫使他离开苏丹那片熟悉的土地。与许多前来避难者一样,约旦对他而言,更多是一个临时的落脚点,而非永久的家园。在这里,他努力适应陌生的环境和文化差异,打工、学习英语,梦想着未来有朝一日能移居海外,寻求更稳定与公平的生活。然而,他所面对的困难远超想象。 生活中的黑色难民常常感受到来自当地社会的排斥。尽管他们多年来融入城市生活,始终无法摆脱身份标签。
约旦社会中某些人会用“abu sumrah”这一带有贬义的词汇来称呼他们,它源自阿拉伯语中“asmar”即棕色或褐色的词根,但被赋予了种族歧视的色彩。如此称谓剥夺了他们作为个体的独特身份,使他们在社会边缘愈加孤立。歧视不仅止于语言层面,甚至渗透到商业产品中,例如一款在阿拉伯世界较为流行的巧克力奶油饼干被称作“Ras al-’Abed”,意即“奴隶头”,这在无形中反映了在某些角度上的种族偏见。 法律地位的缺失是黑色难民所面临的另一重要挑战。约旦政府未对大部分难民给予官方身份承认,这意味着他们无法享受诸如劳动许可、教育权益等基本权利。许多难民被迫从事非法或地下经济,遭遇劳动剥削,工资被拖欠,甚至身陷现代奴隶制的困扰。
许多女性,尤其是来自肯尼亚、乌干达和加纳的难民,在被引荐到约旦做家政时,被误导关于薪资待遇和工作强度的真实情况。一旦逃离这些工作安排,她们不仅失去生计,甚至面临拘留和驱逐的风险,其生存环境脆弱且极端。 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约旦迎来了大量叙利亚难民。在国际援助和资源紧张的背景下,大多数援助集中向叙利亚难民倾斜,这导致较早进入约旦的苏丹、南苏丹、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等非洲国家难民被边缘化。他们等待国际救助的时间更长,获得的机会较少。值得一提的是,叙利亚难民在约旦普遍能享受更多合法权益,形成了当地难民待遇的阶层分化。
2015年,约旦政府开始加大对黑色难民的驱逐力度。这一年12月初,数十名苏丹难民在安曼联合国难民署总部前发起和平抗议,诉求改善生活条件和加速重新安置。但突如其来的警方镇压打破了抗议现场的宁静。凌晨时分,警察将难民们胁迫上车,大部分被遣返回战火纷飞的苏丹。此举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谴责,因其明显违背了“不驱回原则”,即不得将难民送回可能导致生命危险的境地。尽管如此,遭遇驱逐的人数依旧超过八百。
在这样的压制环境中,黑色难民不得不依靠社区自救与互助。非营利组织Sawiyan应运而生,提供教育、对话平台及研究支持,聚焦黑色难民在约旦遭遇的诸多挑战。尽管组织努力与联合国难民署和政府进行对话,希望推动政策变革,回应黑色难民的诉求,但真正的改善仍显有限。世界环境变化,政策不断调整,加之旅行禁令的实施,更令他们的出国移民计划艰难重重。难民群体在约旦的生存状况如履薄冰,时刻面临不确定的未来。 虽然生活中充满艰辛和无奈,但伊布拉欣和他的同胞们依旧怀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
街头的苏丹咖啡馆、小型餐厅和理发店成了他们的精神避风港,在这里,他们可以卸下沉重的身份标签,重新找回自我。“这里是我们的舒适地带,”伊布拉欣微笑着说道。在这里,他们不仅仅是黑色的难民,更是朋友、学生和梦想家。他们相互扶持,共同抵抗着社会的孤立和压迫。 黑色难民在约旦的故事折射出更为广泛的难民问题和国际社会责任缺失。从官方的不承认,到社会的歧视,从辛苦劳作中被剥夺权益,到无望的被送回前线,他们的处境极其艰难。
但他们的韧性和希望依然照亮黑暗角落,引导他们向着更公正、尊严的未来迈进。 要理解约旦黑色难民的多重身份与困境,必须关注种族、政治和国际法律的交织影响。他们既是苏丹复杂内战的受害者,也是全球难民政策失衡的受压者。这一群体的命运不仅关乎中东地区的稳定,也提醒全球共同体深化对难民权益的保障。只有通过加强法制保障、提升社会包容、促进国际合作,才能为这段被忽视的历史书写新的篇章。 在中东这片古老而复杂的土地上,黑色难民正努力擦亮他们的名字,而非被污名化的称谓所定义。
他们用微笑和问候,承载着对和平与归属的渴望,呼唤着世界的聆听与回应。随着全球政治气候的变化,国际社会是否能够回应这些呼声,为他们铺就一条通往新生活的道路?约旦的黑色难民,正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等待着属于他们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