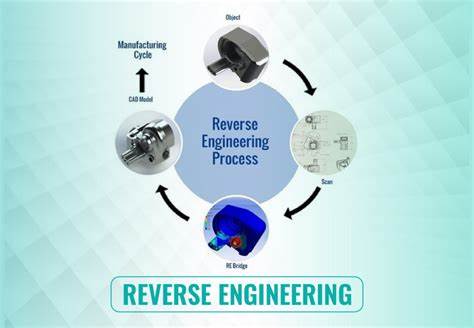墨里尔·斯帕克,这位20世纪英国文学的重要人物,身世复杂且充满传奇色彩,她的作品与人生共同编织出一道独特的文学风景线。斯帕克深刻热衷于传记写作,同时又对自己的传记充满抵触,矛盾的态度为她的文学和生命增添了难以磨灭的神秘气质。她身上的“幽灵”不仅存在于她的小说中,也暗中游走于她的生命轨迹和作品之间。 作为一名严谨的作家,斯帕克从未轻易忽视生命的开端与终结。她的作品《瘦弱女孩》以“很久以前,在1945年”这样富有仪式感的开头和结尾,呈现了时光的闭环。而她擅长使用跳跃叙事手法,将人物最终的命运提前揭示,如《简·布罗迪小姐的黄金时代》中那个在酒店火灾中丧生的玛丽·麦格雷戈,和《司机座位》里被谋杀的莉丝,这种对结局的早期明示无不让读者感知到生命的无常和命运的不可逆转。
斯帕克的人生仿佛也在重复她作品中的主题。她在《课程简历》中草草收尾于1957年自己第一部小说《安慰者》的发表时刻,这本自传性质的回忆录只涵盖了她早期的生活。她对自身故事的掌控欲望极强,72岁时就已经开始筹划如何掌握自己故事的结局。与此同时,她主动邀请了文学批评家马丁·斯坦纳德去撰写她的传记,巧妙地将个人经历和外部视角相互交织。 然而,斯坦纳德交付的初稿令她大失所望,长达1200页的内容被她视为“斧头活”,充满了莫须有的侮辱和诽谤。她认为自己被刻画成一个没有幽默感的陌生人,一个虚构的人物。
此后,她采取多种手段阻挠这部传记的出版,以至于双方陷入一场复杂的“鬼魂之舞”,生者与逝者的边界模糊,追逐与被追逐之间充满紧张张力。 斯帕克一生留存了大量文献资料,她对过往的执着使得她的档案室堪比机场塔台那么高,档案的长度与奥林匹克游泳池相当,宽度更可比拟波音777飞机的翼展。这些珍贵的档案被分别保存在苏格兰国家图书馆和美国塔尔萨大学的麦克法林图书馆,成为法庭上“无声且客观的真相证据”。对斯帕克而言,事实是她最坚实的防线,也是对抗误读的最佳武器。 她的作品深受她早年从事传记写作的影响。作为一位传记作家,她理解开始和结局的重要性,也洞察人物命运的整体脉络。
她的第一本成书《光之子》是关于玛丽·雪莱的传记,书中她强调无论故事如何演绎,无法改变玛丽·雪莱生于1797,逝于1851的基本事实。巧合的是,斯帕克本人正出生于1918年2月2日,这也是玛丽·雪莱逝世之日。这种时间上的交织为她对生命与写作的看法增添了超现实的色彩。 斯帕克的个人经历同样充满戏剧性。她19岁那年移居南罗德西亚(今津巴布韦),嫁给了一位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教师,婚姻很快破裂,儿子留在修道院,而她回到战时的英国从事黑色宣传工作。战后她管理诗歌协会,继而投身批评家与传记作家的生涯,艰难度日的岁月最终在她1954年皈依天主教和完成处女作《安慰者》后得以拨云见日。
自此,声名鹊起,创作生涯进入黄金阶段,随后陆续出版了二十余部公认完美的小说。 作为文学艺术的总结者,斯帕克对传记的诠释富有独到见解。她曾指出传记的本质在于总结,而她深谙总结之道,能够将厚重纷繁的人生细节凝炼成优雅的文体。其作品涵盖短篇小说、传记、批评论文、诗歌及文学编辑,虽然篇幅精炼,但背后却是山一样厚重的档案资料和细致考证。 斯帕克告诫传记作者“当我已经死去,请像对待鬼魂一样对待我”,这一表述不仅是对个人人格独立的宣示,也是她对传记写作境界的抒怀。在她的小说中,鬼魂频频出现,既是恐怖的象征,也折射出生者的心理阴影。
如短篇《波多贝罗路》中被草堆窒息致死的娜德,死后化为怨灵纠缠凶手;另一短篇《执行者》描绘了一位苏格兰作家死前管理散乱文稿的故事,强调了未竟之作的神秘和死后作品的自主性。 斯坦纳德作为研究者,努力从庞杂的材料和访谈中还原斯帕克的生命全貌,但九年过去,双方矛盾不断,斯帕克对被写成“一个虚构的人”感到被背叛和愤怒。她的精神压力乃至健康都大受影响,许多朋友认为这场“传记风波”最终杀死了她。2006年斯帕克去世后,不断修订传记的斯坦纳德直到2009年才完成并出版了最终版本,获得广泛好评,被视为传记写作的典范之作。 那么,为何一位私密性极强,又渴望掌控生命叙事的斯帕克,会邀请他人代为书写?这一悬而未决的谜团也许正是她另一个形象的“幽灵”。她其实在生命中多次书写过自己的传记,但多是以自我与传记作者复杂互动作为主题,反复探讨传记与真实的边界。
在其作品《佩克汉姆的叙事歌》中,由恶作剧者杜格尔·道格拉斯为退休女演员玛丽亚·奇斯曼“代笔”,却始终引发关于事实和虚构的冲突,凸显自传与假传记之间的迷局。斯帕克以这种错综复杂的叙事,映射出自我认知的多面和传记艺术的曲折。 她对传统传记的批判也深刻且扎实。她曾强调,单纯事实的堆砌无法呈现复杂人物的立体真相;传记必须目睹冲突,才能展现一个真正的“完整的人”。就如她分析《科学怪人》中的弗兰肯斯坦与怪物,二者虽独立却又密不可分,宛如传记者与被传记者的共生关系。正因为这种彼此缠绕,传记也许永远无法做到客观分离,而更像是一场身份和艺术的共舞。
《安慰者》中的女主角卡罗琳·罗斯正是斯帕克的投影,她意识到自己的思想正被某个无形的幽灵记录着,正如作者本身在书写过程中所感受的命运控制。卡罗琳试图抵抗,甚至破坏这场“小说的计划”,表达了对被写入故事的深刻焦虑。这既是对文学创作的元叙事,也是斯帕克人生独特境遇的象征。 因此,墨里尔·斯帕克的生命与写作不可分割。她既是幽灵的创作者,也是被幽灵追寻的存在。她在作品和生活中不断探索自我认同、时间与命运、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展现了文学和传记艺术的复杂魅力。
她对传记的热爱与厌恶、掌控与叛逆、明示与隐晦,构成了她非凡人生的一道独特风景。 墨里尔·斯帕克以一种独特的文学语言和人生哲学,留下了深刻的艺术遗产。她让我们反思生命的书写与呈现,提醒我们在真实与虚构之间,铭记不断被书写的“幽灵”如何塑造我们对自我和历史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