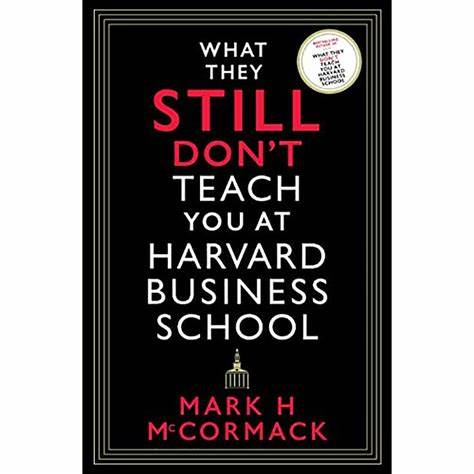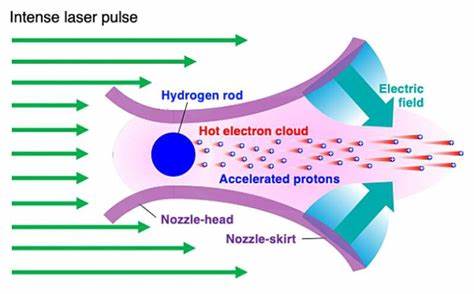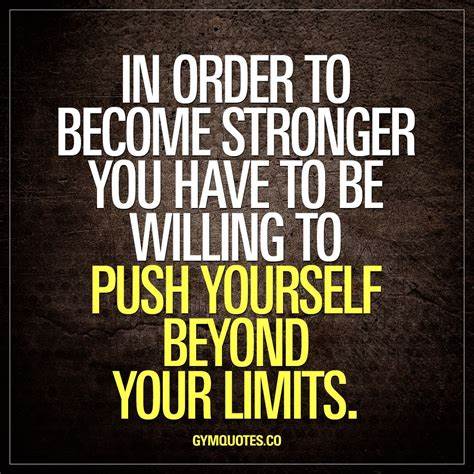现代商学院的领导力课程往往强调视野、赋能和魅力,传递出积极向上的领导形象。然而,历史、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结果却为我们揭示了权力的另一面——它如何诱惑、腐蚀甚至摧毁人。权力不仅塑造了领导者的行为模式,更深刻影响着企业文化和社会环境。透过心理学研究、脑部扫描和刑事法庭的庭审文献,我们能够见到权力带来的黑暗习性,并认识到这些行为与现代商业实践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权力的魅力远非单纯的领导艺术,更多的是暗藏着隐藏的危机。权力总是吸引着骗子、阴谋家和操纵者。
心理学中的“暗三角”人格——自恋者、精神病患者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在领导层中有着不成比例的高出现率。尽管他们的表现往往低于平均水平,甚至带来更大损害,但他们却能迅速爬升到权力巅峰。自恋者因其极度自我关注和自信,表现出极强的说服力和曝光度;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则依靠狡诈和操纵建立同盟,从而在企业内部构建霸权;精神病患者表面看似有魅力且冷静,但却极度冷酷无情、冲动且缺乏悔意。此类人格的领导者往往更关注短期私利而非企业和社会的长远发展。权力本身并非中立,反而对人格的阴暗面形成一种不健康“吸引力”。研究显示,约有三至四成企业高管具有某种程度的精神病特质,这远高于社会上的平均人群。
此外,精神病倾向在企业学生群体中的比例偏高,说明权力的吸引使得这些个体主动进入权力竞争的战场。权力成为他们实现个人欲望的捷径,也使得企业成为他们施展操控策略的舞台。精神病态领导者掌权往往经历五个阶段:最初通过魅力和慷慨建立关注与支持,随后通过分化“内外”实现对组织的控制,逐步消除监管机制并掌控信息流通,以恐惧统治一旦权力稳固,最终通过神话化重塑历史,掩盖其所犯下的错误。企业中的表现则是任用忠诚的支持者,打压敢于揭露真相的吹哨人和研究者,进行大规模裁员以恐吓员工,以“环境、社会与治理”(ESG)为幌子进行公关重塑,利用授权传记美化形象,以及通过税务漏洞进行所谓的慈善捐赠。上述行为无不突显了“目的即手段”的暗面思维。与此同时,大多数人在面对强权时选择服从,即使内心觉得不妥。
现代再现的米尔格拉姆实验显示,70%的成年人仍会执行不道德的指令,坚守权威的影响力依然强大。斯坦福监狱实验和BBC监狱实验进一步证明,普通人在赋予权力后,会迅速展现出残酷和非人化的行为。权力如何扭曲人性,主要在于个体对权威的默认服从。正如法兰克福学者哈娜·阿伦特所言,“恶的平庸”即是因顺从而非因极端恶意产生的暴行。人们遵从不道德的领导,往往不是出于天性邪恶,而是相信自己无从选择。这种“顺从模式”在神经科学层面被称为“责任感降低”,人体在执行命令时,情感共鸣和负罪感的神经活动会被抑制,造成伤害他人时心理负担减轻。
令人震惊的是,遵守命令通过神经回路的改变甚至影响着个体决策,使人将自主选择误认为是命令驱动,从而削弱了抵抗非法和不道德命令的能力。抵抗权威需要大量的认知资源,也即真正的勇气是昂贵的,而大多数人自然倾向于节省心理能量,从而屈服于权力安排。权力还极大降低了领导者的同理心,使其更易伪善和虚伪。他们往往会指责他人的不当行为,但自身行为却更加严重。权力大的领导者失去对他人情绪的准确感知,决策时忽视甚至误读他人观点。然而,当权力伴随着问责机制和有意识的换位思考时,有可能优化公平性和领导质量。
但现实中,暗三角型人格总是在问责漏洞中利用权力为己谋利。腐败几乎是权力体系中的常态。历史上知名的企业丑闻如伯尼·麦道夫、安然公司、Theranos和Wirecard均揭示出高管滥用权力和欺诈对经济与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危害。罕为人知的是,某些企业高管更涉及严重的人权侵犯案件。纳粹时代的IG法本公司高管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犯下反人类罪,而当代诸如福特、埃克森美孚、壳牌及雪佛龙等跨国公司亦涉及谋杀、酷刑、性暴力和对冲突地区的支持等丑闻。此外,社交媒体巨头Meta在埃塞俄比亚内战中的偏袒和忽视责任,使其助推了仇恨言论的蔓延,暴露出技术平台在地缘政治冲突中的负面作用。
这些案例表明,企业法人的有限责任制度或复杂的子公司结构使得高管个人后果难以显现,却并不减轻其道德上的责任。这种“拼贴式”决策模式将大量死伤化作财务报表中的数字,使得屠杀和破坏在冷漠的商业计算中变得微不足道。尽管高层领导中有一定比例会举报下属的不当行为,但却对同级领导的违规闭口不言。调查显示,管理层中举报比例虽高于非管理层,但举报对象集中于下属而非同辈,导致高层腐败案件大部分未曝光。由于高级执行人员犯错造成的损失远高于普通员工,这种沉默加剧了制度风险。面对职场权力的黑暗面,唯有构建更具韧性的组织体系,方可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
一个行之有效的保护机制包括建立匿名举报渠道并充分保障吹哨人安全,只有这样才能发现更多隐藏的舞弊行为。其次,权力结构的分散和任务决策的共享,能够有效减少对单一权威的盲目服从,促进理性的质疑和监督。定期轮换领导职位也有助于抑制因利益关系而形成的同盟,降低权力腐败的概率。针对潜在的暗三角人格,可引入简便的心理筛查工具,如“肮脏十二项”,辅助识别高风险领导候选人,提前预防权力滥用。传统的商学院教育多强调领导力的光辉面,却鲜少涉及权力的阴暗实质。权力不仅仅是管理技巧,更是一场社会心理和神经生物学的深刻博弈。
从巨大跨国企业的历史案例到现代制度设计,我们看到权力的游戏规则其实千年未变,只是换了个名字。最终,建立伦理的领导力,需要我们超越人格的局限,将关注点放到系统构建与文化培养之上,使权力真正服从于社会整体的利益。从而,企业才能摆脱昔日的弊病,迈向一个更加透明、公正与人性化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