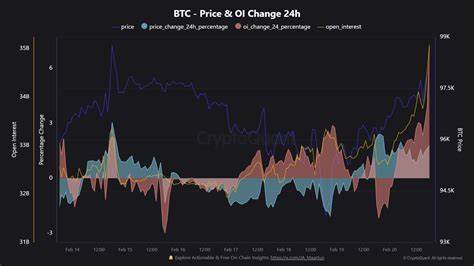爱德华·伯拉,这位20世纪英国画家的艺术旅程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人生如同一趟穿越岁月的巡礼,横跨多个国家和文化场域。作为一名具有显著个人风格的画家,伯拉的作品不仅反映了他丰富的社会经验,更展现出他对时代潮流和亚文化的敏锐洞察。他的画笔记录了从巴黎夜晚的歌舞到纽约哈莱姆文艺复兴,再到西班牙内战前夕的紧张气氛,乃至二战时期英国海边军营的瞬间,犹如一部以颜色和形态织就的二十世纪缩影。 伯拉的艺术生涯颇具独特性,他既是现场的见证者,也是亘古不变的旁观者。他曾身处1925年巴黎,亲眼目睹约瑟芬·贝克在《黑人评论》中的首次惊艳亮相,也曾远渡重洋,深入哈莱姆的舞厅和酒吧,感受那座城市的爵士乐与多元文化碰撞。他追随作家马尔科姆·洛瑞的脚步,游历墨西哥,并身处西班牙那即将陷入内战的紧张氛围之中。
二战期间,他定居于英国海岸小镇莱,目睹士兵们往返前线,亲历战争带来的种种复杂情绪。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又以敏锐的目光关注现代工业化对英国乡村景观的侵蚀,描绘高速公路和高压线穿越古老山林的景象。 从艺术流派的角度看,伯拉既与当时的先锋派画家有交集,同时又坚守个性,不被任何艺术派别定义。他生涯中曾短暂加入保罗·纳什主持的Unit One艺术团体,并曾与毕加索、米罗、马格利特等传奇艺术家一道,在1936年的伦敦国际超现实主义展览中展出作品。但他本人坦言不愿被人“告知应该如何思考”,体现出他独立而倔强的艺术精神。 身体健康的困扰是伯拉艺术道路上的一大挑战。
童年时期他患过肺炎和风湿热,成年后长期受风湿性关节炎和贫血折磨。正因如此,他偏好用水彩而非油画,水彩这种在桌面上作画的方式减少了身体负担。尽管身体疼痛,伯拉却在绘画中获得了内心的解脱,他曾写道:“唯一让我感受不到痛苦的时候,就是当我在工作的时候。” 伯拉社交广泛,拥有艺术家、作家、编舞家等多领域的朋友,如作家安东尼·鲍威尔和编舞大师弗雷德里克·阿什顿等。他喜欢结伴旅行,与朋友们共享艺术与生活的欢愉。无论是在巴黎闪耀的歌舞厅,还是在马赛的水手酒吧,以及哈莱姆那些灯红酒绿的舞会和脱衣舞俱乐部,伯拉都全情融入,捕捉那些充满生命力与奇异色彩的瞬间。
然而,他多数时间生活在英格兰莱的家中,那里舒适宜人,台上播放着他收藏的爵士乐唱片,那些音乐成为其艺术创作的灵感重要源泉。 伯拉的艺术风格丰富多变,尤其擅长描绘20世纪20至30年代的巴黎与纽约社会画面。作品中充满了饱满的人物形象:紧身西装的水手、舞台上的滑稽歌舞表演、喧闹的哈莱姆舞厅。这些作品介于讽刺和夸张之间,反映出其对当时性别、阶级与身份流动的观察与体验。生活在同性恋文化圈,让他感受到了当时少数群体的自由与解放,也激发了他创造出跨性别、颓废又充满魅力的人物形象。有人将他的画作比作布鲁盖尔或扬·斯坦的现代变奏,将那种群像的喧嚣和混乱引入到更为当代和多元的背景中。
从表现形式看,伯拉运用水彩层层叠加的技法,赋予画面深厚色彩与丰富渐变,堪比油画的质感和细腻度。他的人物往往眼睛白皙,仿佛被酒精和迷幻状态所笼罩,透露出似醉非醉的状态和潜在的危险氛围。与德国同代艺术家奥托·迪克斯和乔治·格罗斯带有尖锐批判性的作品不同,伯拉更专注于社区生活和多样群体的肖像,虽有嬉笑怒骂,却不乏温情与包容。 1930年代,伯拉的艺术受西班牙内战影响极大。1933年他前往西班牙寻找类似哈莱姆的热烈氛围,发现弗拉明戈的狂热与色彩斑斓,但同时目睹了暴力和社会紧张局势的升级。与当时许多左翼艺术家和作家不同,他并没有明确支持共和派,甚至在二战期间表示亲弗朗哥,但此言论更像是挑衅。
他对政治的态度复杂且模糊,同法西斯和共产主义都持有反感。 这段时期,他创作了多幅大型作品,采用多张纸张拼贴的形式,画面人物体态夸张,肩膀、臀部和小腿等部位肿胀异常,如同16世纪曼纳主义艺术家朱利奥·罗曼诺的壁画风格。画中形象面目模糊,仿佛来自一种不确定的中世纪背景,却带有戈雅讽喻性与时代的残酷,隐晦而深邃地反映了战争与暴力的无常。 对于战争,伯拉充满厌恶和恐惧。在家乡莱目睹年轻士兵准备奔赴欧洲战场时,他捕捉到士兵们既严肃又阴沉的神态,画作如《士兵背影》(1942)和《莱的士兵》(1941)中,士兵们带着类似瘟疫面具的形象,显得既戏剧性又威胁性。他将对战争的噩梦和社会痛苦凝聚成画,传达出一种无力的愤怒和悲伤。
他曾写道,自己对世人面孔感到恶心和恐惧,自己的愤怒情绪仿佛毒瘤一般悬在空气中。 尽管如此,伯拉也通过为皇家歌剧院和萨德勒斯韦尔斯设计舞台服装和布景,从《卡门》和《唐·吉诃德》等作品中获得创作的喘息和乐趣。然而,战争折射出的阴影始终萦绕心头,成为他艺术创作中不可磨灭的背景。 从三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伯拉的视野又回归到英国乡村景观。他被园艺的兴趣和轮游英国的公路旅行激发,创作出多幅自然景观画作,如1972年的《惠特比附近》和1946年的《鸟人吹笛者与渔女》,融合了现实与民俗元素。此外,他也关注现代工业的发展带来的冲击,画中出现加油站的蛇形油管、咆哮的车辆长龙向乡村进军,营造出现代与传统的张力。
在1952至1954年间的《骷髅派对》中,他将墨西哥亡灵节的骷髅形象巧妙融入工业场景,寓意着死亡与庆典并存的复杂感受。 面对外界对其作品意义的探问,伯拉曾坦言“我从不向任何人透露任何事……我认为那无关紧要”。他的作品正是在矛盾与神秘中构筑出一幅多维的二十世纪图景,从爵士乐的欢乐舞步到战争的无情哀歌,展现了一段历史与文化的浓缩与升华。 位于伦敦泰特不列颠美术馆的新展览集中展出伯拉的代表作,细致揭示了这位难以归类、内容丰富的画家的独特世界。展览不仅展现了他的艺术才华,也让人们得以穿越那段充满变革与不安的20世纪,回望那些嬉笑怒骂、光怪陆离的群体与文化,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他对当时社会边缘群体的关怀与描绘,以及那份诡谲又绚丽的艺术情感。通过伯拉的画笔,二十世纪的文化多样性与人性复杂性跃然眼前,成为永恒的艺术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