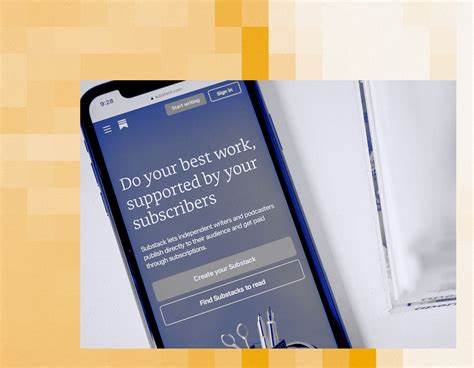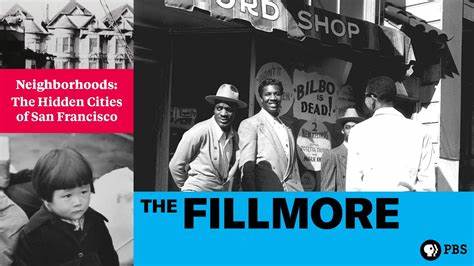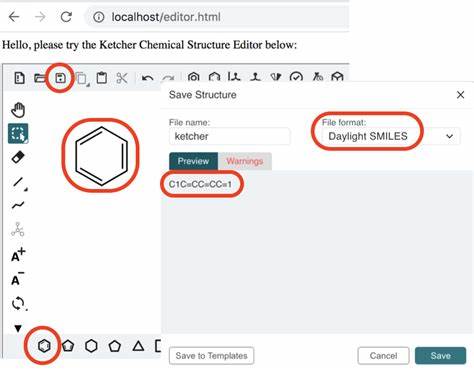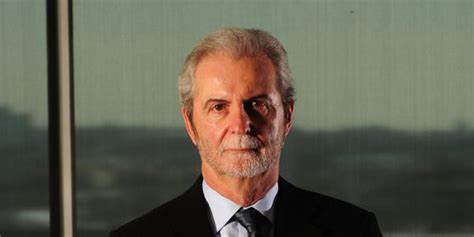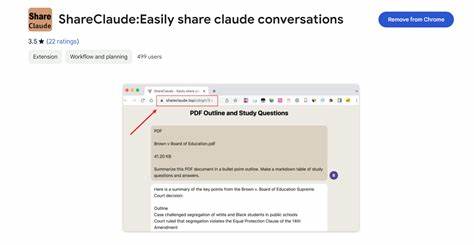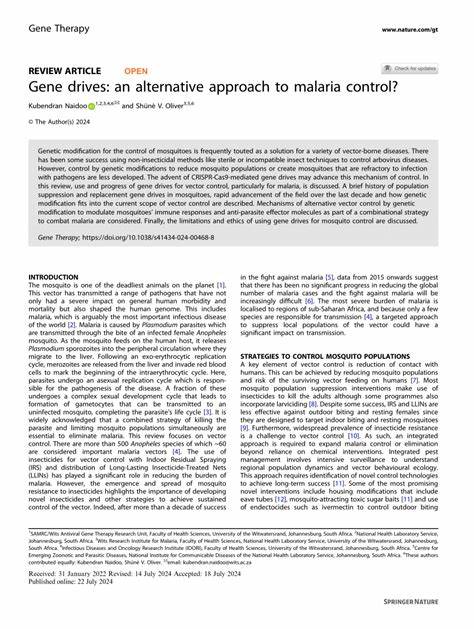近年来,Substack作为独立写作者的聚集地和创收平台,再度引起媒体行业的广泛关注。该平台以其“编辑自由”和“订阅变现”的优势,吸引了大量传统媒体出身的知名记者和评论员。尤其在2025年,这一现象更加显著,众多被传统媒体约束或辞去职务的新闻人纷纷选择在Substack上创办独立订阅栏目,寄望通过直接付费获得更大自主权和可观收入。Substack的这种写作生态一度被视作新闻业未来的救赎和创新突破,甚至引发了整个行业对于传统新闻机构留人保才的紧张。然而,Substack的辉煌背后也伴随着诸多隐忧,订阅疲劳、内容良莠不齐、平台定位模糊等问题逐渐暴露,时间正悄然逼近这场“独立写作革命”的关键节点。Substack吸引知名记者的核心魅力在于,“没有主编干预,没有广告主的审查”,一切写作内容由创作者自主掌控。
和传统媒体那种新闻内容受限、公式化和商业压力巨大的环境不同,Substack允许作者展现个人观点、深度话题和不同声音。譬如,前ABC新闻记者特里·莫兰因言辞冲突被电视台解雇后,迅速在Substack上开设了公众号,发布大量政治评论,获得超过十万免费关注者。这种“自由表达”的氛围使不少有志于突破传统新闻束缚的记者看到了新的生存和发展路径。Substack CEO克里斯·贝斯特曾骄傲地表示,该平台已有超过50名创作者年收入破百万美元,这样惊人的数据更是吸引了大量名人和意见领袖加入。然而,辉煌数据并不能掩盖订阅模式的内在瑕疵。首先,Substack的收费机制决定了接收优质内容需要不断支付多项订阅费用,这对于广大普通读者来说成本不菲,存在严重的“订阅疲劳”现象。
通常,一个作者的订阅费用月费在5至10美元,年费从50至150美元不等。而一旦想要跟踪多位作者,费用就如滚雪球般快速增加。有读者透露自己每年为30多个订阅服务投入超过2000美元,这显然远超大多数人的承受能力。相比之下,许多传统媒体机构提供的“全包式”订阅更具性价比。例如,著名作者德里克·汤普森从《大西洋》离开后,在Substack上的年费订阅高达80美元,而《大西洋》数字版整年订阅费用却接近此价且内容更丰富。此外,Substack写作者的受众极其有限。
独立订阅机制意味着大多数“付费读者”只占整体关注者的一小部分,使得很多作者的声音无法广泛传播。这种“闭门小圈子”的付费阅读模式,使他们难以进入更大的公共话语空间,对于想影响更广泛受众的写作者而言,是巨大限制。内容质量方面,虽然有少数顶尖作者表现优异,但平台整体内容参差不齐,甚至还有不少“无聊”、“业余”和“极端”内容泛滥,尤其是缺乏严格内容审核的自由放任带来了争议。例如凯西·纽顿离开Substack转投Ghost平台,原因之一是对Substack管理团队反对极端仇恨内容态度不满。多位媒体评论员直言,Substack整体内容生态并不稳定,甚至戏称其如“太空探索发射般充满不确定性”。此外,Substack自身也在尝试改变,逐渐摆脱纯文字创作平台的形象,向文化、视频及播客领域拓展,以寻求更多增长空间。
营收方面,Substack据传年收入约4500万美元,旗下创作者及平台的估值约达7亿美元,但这与之前融资阶段的估值相比可能并未有大幅提升,凸显投资者对其商业模式是否可持续持谨慎态度。一些业内分析认为,Substack试图以媒体公司的形象定位自己,却又有意塑造成科技公司的估值路径,这种定位上的矛盾将成为其发展的绊脚石。外部推广也是新入驻Substack写作者面临的挑战。由于Twitter等社交平台影响力减弱,新作者难以获得精准推荐和曝光,导致订阅增长变得更加艰难。对于刚刚开始独立写作生涯的记者来说,启动期的困难远超早期用户。业内人士警告说,Substack的黄金窗期正迅速关闭,新进者若无强大粉丝基础,很难复制“特里·莫兰”式的成功。
面向未来,Substack必须解决订阅成本高、内容管理松散以及推广渠道受限等问题,才能维持平台的活力和信誉。同时,读者对“多订阅服务”累积带来的疲劳感,促使市场呼唤更加灵活、优惠的短期订阅套餐和试用机制。只有同时兼顾内容优质性和用户体验,Substack才能在日益激烈的数字内容订阅市场中找到可持续的生存之道。总体来看,Substack代表了数字媒体变革中的一次重要尝试,它让独立记者拥有了更广阔的话语空间和创收渠道,挑战了既有新闻出版的传统格局。但同时也暴露了独立订阅生态下商业模式和用户接受度的复杂矛盾。未来的数字新闻格局,或许将更依赖于如何在“内容自由”和“经济可持续”之间找到巧妙平衡。
Substack能否延续当下的“高光时刻”,逆转订阅疲劳带来的颓势,成为媒体行业关注的焦点。无论结果如何,这场独立写作的浪潮已深刻影响着新闻传播和内容消费的格局,也为所有内容创作者和消费者带来了值得深思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