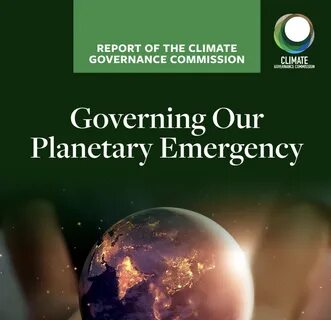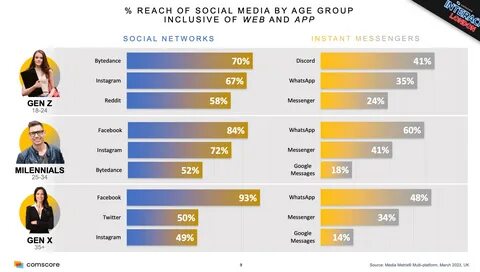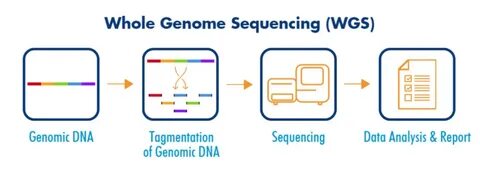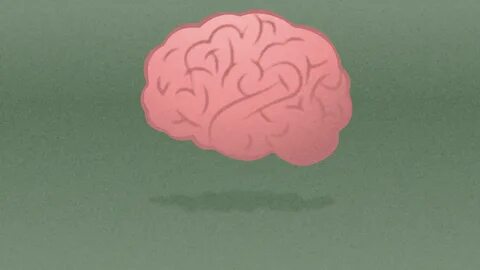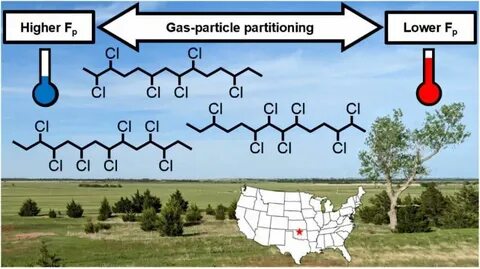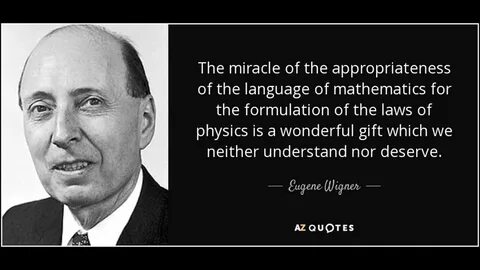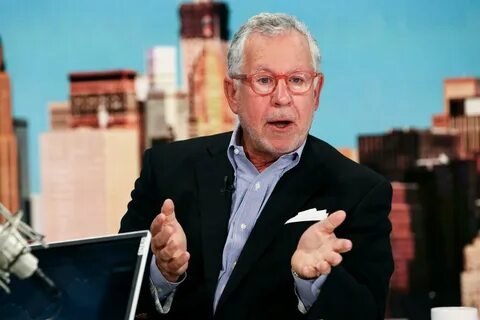当前全球民主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各国国家主权逐渐被跨国机构和市场力量所蚕食,导致民主制度的脆弱性不断加剧。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雷克在其著作《重新掌控》中深刻剖析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家权力向技术官僚机构的转移趋势。施特雷克指出,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并非使市场脱离国家控制,而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单一市场体制,通过国际条约、法律与监管机构强化全球经济统一性的铁幕,从而弱化了国家民主的“集体特殊性”。这种经济统一性的强制推行,不仅剥夺了民主国家针对本国公民特殊利益进行决策的能力,还催生了对权威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的潜在支持,为全球政治的反动势力提供了温床。施特雷克的分析为理解当代反动情绪的起源提供了独特视角,同时在不认可其极端言辞的前提下,启发了建设性替代方案的思考。施特雷克借鉴了卡尔·波兰尼、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赫伯特·西蒙等思想家的理论,提出应将主权权力向下放权至民主国家,因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具备充分民主权能的小型国家网络,有效应对全球经济的复杂性,防止技术官僚脱离民主控制。
在这一路径上,国家不是减少其权利,而是重新掌握对经济的主权管理,进而保障本国公民的公共利益优先。历史告诉我们,现代民主政体无法脱离拥有绝对主权的国家体系。国家的主权在很大意义上就是其民主的前提与保障,一旦国家丧失主权,便如同殖民地一般沦为外在权力的附庸,民主控制和法律权利形同虚设。施特雷克强调,现代社会的国家主权必须涵盖经济决策的领域,正如凯恩斯在1933年提倡的政治经济主权,他主张货物和金融应在国家层面得到充分保护和调控,避免依赖国际市场的无序波动。与此同时,波兰尼指出,没有控制国际经济关系的能力,国家将无法抵御市场的剧烈冲击,民主秩序也就岌岌可危。施特雷克的“凯恩斯-波兰尼国家”理念正是呼吁恢复国家主权,以保障民主不被国际经济体系中失控的力量摧毁。
此外,他也回应了大国难题,认为对于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现存的单一中央集权模式表现出治理无效和民主疲软的双重困境。施特雷克主张推行有效的地方自治和分权,赋予地区更多决策权,形成多层级的民主治理结构。通过将权力下放,国家能够更精准地回应各地区民众的具体需求,提升政治的合法性和效率。而在国际层面,国家间应建立基于平等主权尊重的合作机制,以实现地区和平与多极共存,这对于形成一个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至关重要。对大国解体与小型国家网络化的设想,施特雷克持谨慎态度。他警示,外部势力干预引发的国家分裂容易引发内战和社会动荡。
他指出,尤其是历史上缺乏地方性小规模政治传统的地区,如非洲和某些亚洲国家,过度分裂风险极大,反而可能加剧地区的不稳定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丛林。因此,这些地区应推动以区域多国合作为基础的和平体系建设,借鉴非结盟运动和金砖国家等多极世界的努力,促进包容共存和共同发展。当前大国面临的治理困局是选择市场失灵还是技术官僚失灵之间的两难。大国的经济多样性和地域广阔性使中央政府难以兼顾各地具体实际,单一政策难以发挥效用,治理效果不彰导致合法性受损。而技术官僚操控往往带来民主失效,决策脱离民意,助长了民众的不满和排斥。施特雷克最终提出,民主国家的分解乃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关键在于塑造怎样的政治结构。
他借鉴赫伯特·西蒙关于复杂系统“分解”的理论,建议构建由小而智能的政策单元组成的政治体系,以提升治理的灵活性和敏感度,同时防止新型霸权的产生。对于网络国家(network states)和企业主权等未来政治单元的设想,施特雷克持审慎立场。他指出,任何未来的政治模型都必须回答如何从现状过渡到未来、谁将成为变革主体以及如何获得合法性的基本问题。没有现实路径和群众基础的设想难以实现。作为功能性单一且复杂度远低于传统国家的网络社区,能否承载丰富多元的社会生活和民主议程还有待检验。最终,决定权掌握在公民手中,是投票、是抗争,还是放弃主权,都是他们的选择。
技术的角色同样被施特雷克区分开来。他强调社会是多元复杂的关系网,而国家是具备特定职能的政治组织。技术本身并不能解决民主与国家权力的对立,关键在于技术被谁拥有和设计,是否服务于公众利益还是少数资本。私有化和平台寡头控制的技术工具,反而可能加剧民主贫困。要让技术回归民主服务,依赖的是政治意愿和制度设计,而非技术自身的力量。综上所述,反对全球治理并非拒绝国际合作,而是主张恢复国家经济主权和民主控制,强化地方自治,反对跨国技术官僚体系对民主国家的侵蚀。
这样的路径不仅有助于抵抗反动政治的兴起,也为建立一个公平、有效且多元包容的国际秩序提供可能。国家不应仅仅是国际市场的执行者,而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者和保护者。未来的挑战,恰恰是如何在全球复杂互联的环境下维护这种主权,同时构筑区域和平机制,化解矛盾,实现国家主权与民主治理的良性循环。施特雷克的深刻洞见,为思考当代及未来世界政治格局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