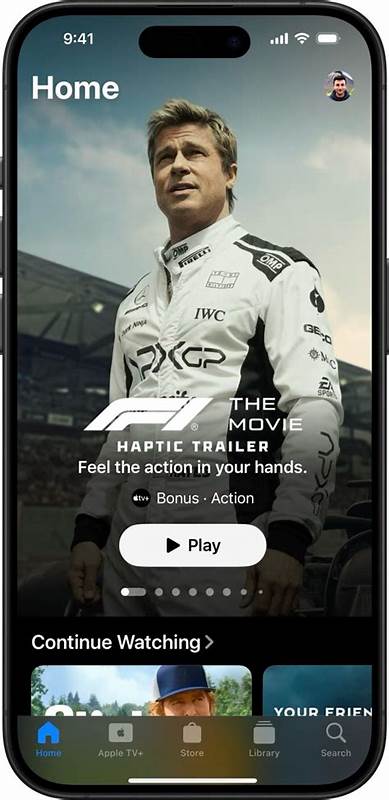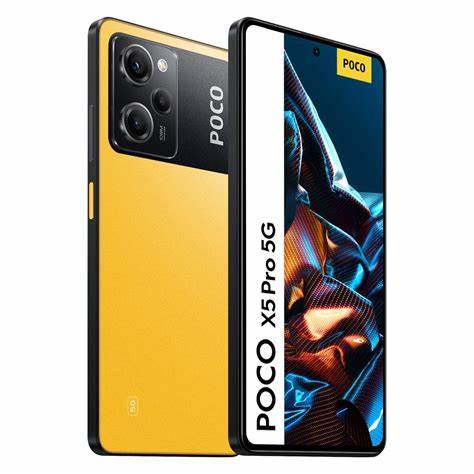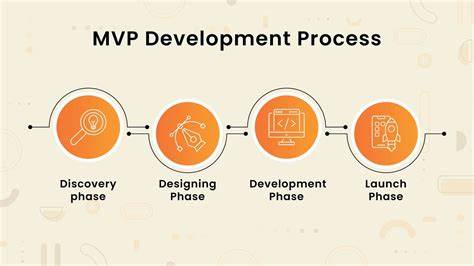近年来,美国住房市场面临前所未有的供应危机。尤其是在过去几十年曾经繁荣的郊区地区,住房建设的脚步逐渐放慢,最终导致现有住房数量远远无法满足需求。据最新研究数据显示,美国目前约缺失1500万套住房,这一缺口对整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产生深远影响。郊区曾是美国梦的象征,是家庭安居乐业的理想选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郊区大量新建住房满足了城市居民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诉求,兴起了如凤凰城、达拉斯、亚特兰大这样的城市。然而进入21世纪后,郊区住房建设速度明显下滑,供应弹性大幅减弱。
核心问题之一源于地方政治和社区对新开发项目的抵制。随着郊区居民结构的改变,尤其是富裕、教育水平较高的新居民迁入,他们往往通过地方立法和规划手段设置门槛,限制新建住房的数量和密度。这种现象在被称为“内生性管制”的机制中表现尤为突出。居民们试图保护既得利益,维护社区环境和财产价值,而这些做法却无形中推高了住房价格,降低了新住房供应的灵活性。另一方面,住房建设行业的恢复力不足也是供给不足的重要原因。自2004年以来,美国房屋开发企业数量锐减,据统计,全国范围内房屋建筑商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建筑业就业也下降了约六成。
虽然部分城市如休斯顿和达拉斯有所回升,但整体行业仍处于低谷。人力和资本的不足进一步制约了新住房的开发速度。成本的提升虽然不可忽视,但相较于香港或旧金山等地的飙升,建筑成本上涨只占房价上涨的一部分。其他因素如土地限制、环保法规及地方审批复杂性等均加剧了建筑难度。令人关注的是,尽管很多郊区仍拥有大片低密度未开发土地,理论上应具备较大的发展潜力,但实际开发速度却远远滞后于需求增长。密度限制并未成为主要障碍,数据反而显示出部分地区密度低、可开发地块充足,却因许可审批难度大、社区反对强烈导致供应停滞。
这种“许可成本”和“邻里反对”的合力成为阻碍郊区市场成长的关键瓶颈。从价格表现来看,房地产价格在2024年创下历史新高,部分城市上涨幅度惊人。迈阿密的房价自2012年以来上涨了超过155%,凤凰城增长也达到157%,达拉斯上涨接近95%。而价格的快速提升反过来冲击了住房可负担性,使得中低收入家庭难以进入市场,也增加了租赁压力。市场的增长动能逐渐从传统强势城市均衡分布,趋向集中少数几个对建设持开放态度的城市,如休斯顿和圣安东尼奥。相比之下,其他过去快速成长的城市如拉斯维加斯、奥兰多等地则出现大幅减速。
研究还发现,地方法规的严格程度对住房建设敏感性影响巨大。引入的Wharton土地利用规制指数显示,规制越严厉的都市区,供应对价格变化的响应越不灵敏,说明政策红线使市场难以灵活应对需求冲击。为何出现如此严重的住房短缺危机?主要是由于住房开发过程中的利益固化与排斥行为。按照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的理论,这类现象表现为既得利益群体通过集体行动来保护自身利益,阻止新增住房进入市场,形成排外性的“租金寻租”行为。这使得许多郊区在潜在的高需求面前,反而形成类似旧金山严格限制住房供应的缩影。此外,住房建设的供需矛盾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广泛影响。
住房价格攀升导致年轻家庭购房困难,影响家庭结构和人口流动,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许多中低收入居民不得不迁入租金更高的城市核心,或是在交通不便的地区忍受长时间通勤,降低了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政府层面的政策回应亟需调整。当前,对缓解住房短缺的传统做法,如增加公共住房投资或提供购房补贴,仍无法触及根本问题。要想缓解短缺,必须从根本上降低地方开发阻力,简化审批流程,加大对多样化住房形态的支持力度,打破业主对社区排外行为的垄断。同时,联邦和州政府应强化对地方规制的监督,推行鼓励适度密度提升的法规,引导住房市场回归健康发展轨道。
展望未来,美国郊区住房建设若能破除政治与社会阻碍,恢复建设行业活力,迎来新一轮增长潜力巨大。广阔的土地资源和人口持续增长趋势依然为郊区发展提供基础保障。不过,这需要住宅开发商、地方政府和社区居民多方合作,积极寻求平衡增长与社区保护的智慧方案。住房市场的活力决定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的幸福感。只有破解供需结构的矛盾,才能确保未来美国郊区依然是充满活力的美好生活之地。总之,1500万缺失住房的背后,是美国郊区多年来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集中体现。
地方制度障碍、业主排外主义、行业活力不足及政策滞后交织导致住房短缺的长期化。形势紧迫,转型创新已刻不容缓。通过开放包容的理念与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美国郊区有望摆脱建筑热潮终结的阴影,重新迎来可持续的住房繁荣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