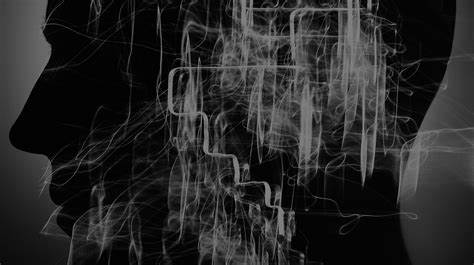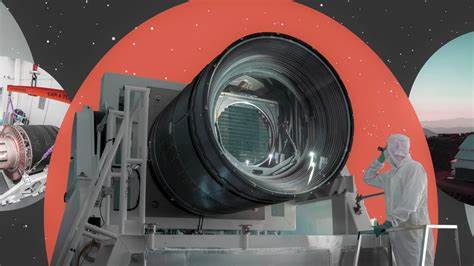在现代社会,算法无处不在,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随着数字技术的渗透,人类身体与机器的界限愈发模糊,体现在行为习惯、身体管理甚至身份认同上。算法时代,人体仿佛开始模仿机器,成为数字网络中运作的一部分。这不仅关乎技术进步,更涉及政治权力的运作以及资本主义演化的深层次转变。 以日常生活为例,许多人不再依赖自己的经验和记忆,而是借助导航软件如Waze指引路线。即便是长期熟悉城市道路的人,也宁愿放弃自身判断,完全依赖算法提供的实时数据。
这种现象反映出人们行为逐渐数据化、机械化,人类不再主宰行动,而是成为算法链条上的执行者或“傀儡”。从心理角度来看,这种“算法驱动”的生活方式正在重塑人类大脑的反应模式,形成与机器相似的“思维范式”。 更为极端的例子出现在网络文化中。网络主播“Pinkydoll”等新兴网络红人的表演模仿电子游戏中无意识的NPC(非玩家角色),通过机械化、缺乏情感的动作来吸引流量。这种“无脑NPC”表演引发热议,反映了当代网络环境下的算法对身体动作和社交行为的塑形效应。算法不仅引导信息推荐,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个体如何“行动”,甚至如何“存在”于数字世界中。
不局限于数字表现,人体对算法的模仿更体现在生物科技和个体健康管理层面。生物黑客Bryan Johnson以严密的数据驱动健康管理著称,利用智能设备、补充剂和精准监测打造逆生长方案。他强调通过算法指导生活习惯和生理指标,认为算法比人类自身生物本能更能高效地管理身体。这种“算法指导的身体管控”体现了现代个体对“客观健康”的追求,同时也是人体被嵌入技术逻辑中的典型案例。 算法驱动的身体管理无法脱离其背后的社会政治环境。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提出的“生物政治”即指出,技术和制度对个体身体施加的规训与监控。
工业时代通过对劳动力身体的管理实现资本积累,而进入知识经济后,人体和心智的优化成为主流。自由市场和“自我管控”的新形态替代了传统的权力强制,以积极激励而非消极禁止塑造主体,形成“心理政治”。这种从“他律”到“自律”的转变,深刻影响着算法时代身体的机器化进程,使个人内化了对数据、绩效和效率的不断追求。 当今资本主义也正经历转型,数据成为核心资源,平台经济继而形成新的“技术封建主义”。像亚马逊、Meta、X这些巨型平台控制信息与资源,就如同封建时代的贵族和土地所有者。数据不仅是技术资本,还成为对人口行为的大规模监控和预测工具。
数据主义兴起,强调一切皆可量化、一切皆可数据化,情感和主观经验被数字指标取代,整个社会被算法监控体系掌控,这种数字化统治是福柯无法想象的全球级圆形监狱。 在这个背景下,关于最优“产出者”身体形态的讨论出现了分歧。一种观点认为,随着AI和自动化不断取代传统工作,未来人类只需成为像机器一样的“无意识代理”,成为社会运转的能源和数据源。此观点悲观,担忧人类特质如记忆、文化和情感被消解,人类沦为纯粹的数据单元。像Pinkydoll的机械表演和Bryan Johnson的生物算法控制被视为系统的先行预演,昭示人类未来被机器替代的命运。 另一些观点则持较为乐观态度,认为人机融合不可避免且已在加速。
诸如假肢技术、脑机接口和随身智能设备使人体成为半机械化的存在。支持者把DNA视为“软件”,相信未来人类可通过“软件升级”实现疾病根除、意识扩展甚至永生。技术幻想虽充满乌托邦色彩,但也存在深刻的社会不平等风险,科技富豪可能垄断永生技术,社会阶层进一步分裂,甚至出现“赛博格统治阶级”与“原始人类”的割裂。 现实中,技术进步并未带来预期的解放。经济学家大卫·格雷伯指出,资本主义体制下,生产力提升并没有带来社会平等和自由,而是制造了大量无意义的“废物工作”与不稳定就业。技术红利集中在资本阶层,基层劳动者的处境愈发艰难。
左翼力量在应对技术变革时也缺乏有效的替代方案,部分聚焦于否定性质的批判,缺乏建设性的未来蓝图。 女权主义者唐娜·哈拉维提出的“赛博格宣言”对此提供了不同视角。她认为,身体的自然界限和身份认同都已变得可塑且政治化。赛博格作为人与技术混合的象征,不应仅被看作束缚,反而可以成为抵抗控制、重新定义自我的强大神话。技术与身体的交融,既是压迫的工具,也可能成为解放的新途径,这种复杂性使得未来变革充满可能性。 从个人实践角度来看,像Bryan Johnson之类生物黑客的行为,不仅是极致的科技服从,更是对身体极限和生理机制的深入探索。
生物监测设备和算法管理为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工具,也为公共卫生和社会互助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类似地,网络文化里对机器化身体动作的模仿,或许也是一种当代数字审美的表达方式,体现了人类在算法塑造下的再创造和再定义。 进入数据时代的同时,人类社会仿佛迎来了“第二次启蒙”,数据统计成为理解和管理社会的核心方法。历史上统计学与管理国家密切相关,如今数据主义承载了类似功能,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继承了殖民、控制和排斥的阴影。人类未来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伦理与政治的问题。 因此,我们需要探讨的关键不是科学技术是否发展,而是如何构建积极的“技术-生物政治”,寻求个体与社会间的和谐共生。
左翼力量和社会各界应提出建设性方案,推动算法和机器的发展服务于人类普遍福祉,而非加剧异化和剥削。科技与人类能否共同设计出一种新的智慧形态,既接受技术进步,亦保护人文价值,是21世纪必须回答的重要命题。 总的来看,算法时代的人体机器化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挑战的现象。它既是现代技术革命的必然产物,也是我们重新定义人类身份、权力与自由的契机。未来的进程既可能导致人类成为技术的奴隶,也可能促成新的解放形式。在这条道路上,对技术的理性批判与积极探索缺一不可。
唯有透彻理解算法对身体和社会的塑造作用,才能迎接一个既真实又充满可能性的数字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