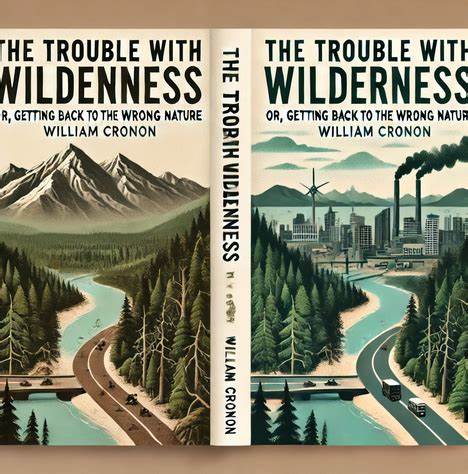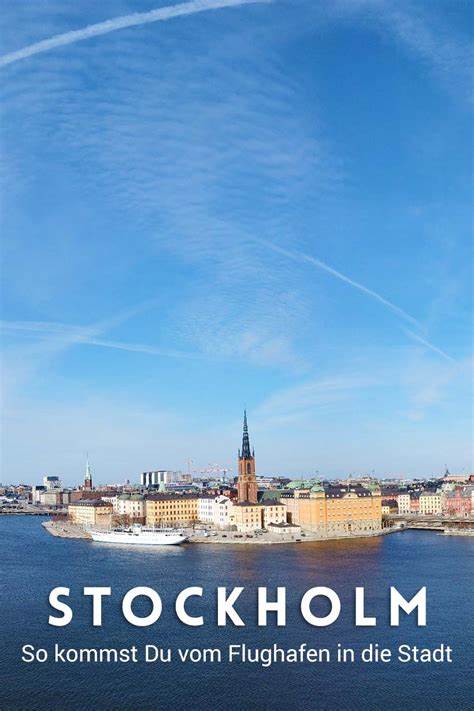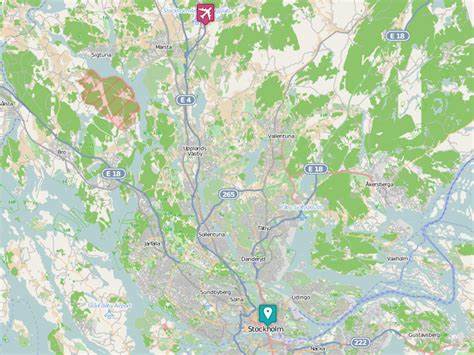"荒野"作为一个被广泛认同的环境保护理念,长期以来被视为人类文明以外的纯净自然之地,是现代环境运动的核心价值之一。然而,现代环境历史学家威廉·克罗侬(William Cronon)对这一传统观念提出了深刻的反思,提醒我们荒野并非是自然的自发存在,而是特定社会文化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构建更加合理的生态伦理和环境保护策略具有重要意义。传统上,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中的"荒野"曾经被视作文明之外、充满危险和恐惧的荒芜之地。早期基督教传统中,荒野是魔鬼试探基督、以色列民族迷失自我的地方,是人类的道德试炼之地。17世纪的殖民者眼中,荒野是贫瘠之地、不毛之地,是待开垦的"废土",缺乏价值和意义。
随着19世纪浪漫主义的兴起,以及西部边疆逐渐消失,荒野的形象被重新塑造。文学家和自然保护运动者如约翰·缪尔(John Muir)与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赋予荒野神圣且崇高的意义,将其比作天堂的花园,是文明的对立面和人类精神净化的圣地。荒野被视为祖国的精神象征,是人类以外的自然维度,是回归原初自我的途径。这种"超自然"的荒野形象,实际上融合了浪漫主义的"崇高"概念和美国边疆神话,既是一种象征性的审美体验,也是一种文化身份认同。荒野不再是令人恐惧的存在,而是赋予了自由、野性和纯粹性的正面价值。边疆的消失导致"荒野"成为过去生活方式的象征,也是对现代工业化、城市化生活的批判与逃避。
荒野精神在较富裕的城市阶层中盛行,这些群体通过旅行、消遣乃至狩猎活动来体验荒野,作为一种文化消费。然而,克罗侬提醒我们,这种理想化的荒野经验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而非现实的自然状态。首先,"荒野"不是真正未被人类触碰的净土。事实上,早期美国西部的荒野地区早已是土著民族世代生存、利用和管理的土地。其原住民的存在和活动被忽视或故意消除,使得荒野呈现出一种"无人区"的假象。这种"空白土地"的神话不仅掩盖了土著人民的权利,也掩盖了人类与自然长期互动的真实历史。
其次,荒野是一种文化想象,其意义更多地反映了现代社会对自身的感觉和欲求,而非自然本身。荒野被想象为人类文明的对立面,似乎只有在远离城市的广袤土地上才能找到"真正的自然",这是人类对现代生活压力的心理补偿和逃避。荒野被神圣化,与其相对的城市被视为堕落、不自然的空间,这种二元对立加剧了人类与自然的隔阂。再次,在环境保护实践中,荒野理念有时反而带来了矛盾和矛盾。例如,为了保护荒野及其中的"纯净"生态,人类活动经常受到限制,甚至将当地居民逐出保护区。这种做法在美国和全球其他地区均有体现,形成"环境殖民主义",将生态保护与社会公正的需求冲突放大。
此外,荒野保护常常只关注广阔且壮美的自然景观,而忽视了那些更为细微或"家门口"的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实际上,我们的"家园"本身也承载着丰富的自然性和"野生性",不应被低估或忽略。克罗侬借助多个文化、历史和哲学角度,提出了重要的环境伦理转向,呼吁人们放弃人与自然的极端二元对立,认识到"自然"与"文化"、野性与人类社会之间是一个连续体。自然不是抽象的异己,它存在于城市、公园、乡村乃至我们的后院之中,这些日常景观同样蕴藏着生态价值和政府责任。更重要的是,环境伦理应当体现对所有生物的尊重和对社区实际生活的关怀,而非单纯强调远离人类活动的"原始"荒野。换言之,环境保护应着眼于"家"的建设,即人人生活其中的地方,通过合理的管理和利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与其幻想逃避文明,不如积极实践批判性的自我意识,选察我们如何对待自然、如何负责任地"留痕"。此种持久而可持续的生态关系建立在尊重"他者"的基础上,无论这些"他者"是森林中巨大的古树,还是市井中的苔藓,亦或是人类社会中的邻居。落脚于此,荒野不再是远方的理想,而是激励我们认识并珍惜日常生活中与自然相连的深刻纽带。最终,真正的野性是存在于我们自身意识中的一种品质,是我们对生命多样性和自然神秘的承认与敬畏。正如诗人加里·斯奈德所言,拥有清晰之心和开放之心的人,无论身处何地,都能感受到荒野的呼唤。荒野的保护不应成为逃避责任的借口,而是唤醒我们承担保护地球家园责任的行动号角。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严峻挑战,破除传统荒野概念的神话,推动一种包容、动态且根植于生活实际的生态文化,才是人类社会迈向可持续未来的必由之路。 。